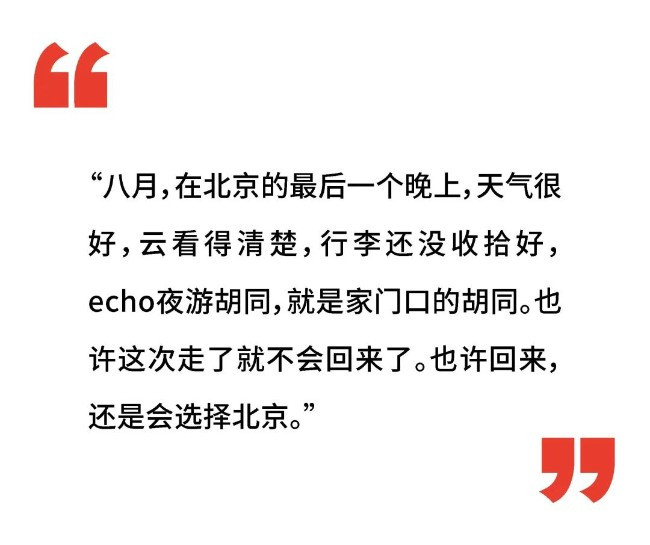
“你只能反复告诉ta,这不是你的问题。”在一期离开北京的播客里,竹子印象最深的是这句话,“这个感受非常普遍。刚离开时候,我会想个人原因和环境因素哪个更大。”今年8月,她离开了北京。
很少会这样,离开一座城市,人们要如此谨慎地反思、审视自己,是不是自己的问题?但北京是个特别的地方。
人教版教材里,每个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就该认识“北京”,它出现在课文《我多想去看看》里:“遥远的北京城,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,……我多想去看看!”
来到北京总是相似的野心或者激励。地图上,北京是雄鸡的心脏。去北京,有出息。
而北京又是个复杂的庞然大物。它创造了许多名词,北漂、朝阳群众、海淀妈妈,人们被北京定义。关于它的文章光怪陆离,《北京零点后》是密集,《北京折叠》则是吊诡。今年六月,北京成为中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,实现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%的目标。
于是,说起“离开北京”,像是逃兵,被竞争、房租和交通压垮,一种被淘汰的失败。
近三年来,“离开北京”这个话题越来越热门,而且人们的去向越来越多元,去深圳、去上海、去成都、回老家、去国外,已经有很多地方可以拿出来和是否留在北京相衡量了。这是怎样的一种趋势,同时也是一个个真实故事发生的情景呢?

20+,
离开北京的 gap year 探索
毫无疑问,竹子在北京已经足够努力,光看她的履历表就可以知道。
从2019年毕业前,到2022年,竹子在北京至少换过五份工作:广告公司、纪录片工作室、文化空间、剧场、媒体……
与此同时,她还在夜里兼职,有时是咖啡店的店员,有时则是酒吧bartender,最晚时清晨六点下班,早上继续上班,精力充沛得像个孩子。
北京满足了她探索的欲望。竹子在东北成长至22岁,学习的广电专业,在家乡一带往往只能找到事业单位的工作,她总是倒在笔试环节。
在北京,工作机会要庞杂得多。剧场那份工作,竹子起先只是想搜索现代舞课程,却找到了招聘启事,几个月后,她就与以色列、加拿大老师,一同出现在舞蹈周节中。另一家文化品牌,竹子则干脆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,在空间里遇到了陈嘉映与刘瑜。
北京永远有最新的东西。竹子刚来北京时,短视频上了风口,无论她在的哪家公司,都愿意试试短视频;疫情之后,她的工作又转成了新晋宠儿——播客制作。
就连兼职的酒吧,在北京也有足够多的划分。一种是她热爱的酒吧,多在东城,譬如school,人群混杂着随意喝酒,聊天才是要紧事。
另一种泛称为三里屯酒吧,由知名调酒师、优秀供货渠道、稳定而资深的投资者组装而成,像一辆福特汽车。据说,部分酒吧有着严苛的规则,着正装进入,消费达标可以进入二层,再往上升,还得有点品味,一种隐喻。竹子的态度是:“我暂时是不太习惯三里屯酒吧。”
在京三年,竹子的工作就在“东城酒吧”类型和“三里屯酒吧”类型中切换,要么是更成熟和商业广告公司,要么是体量更小或更理想化的文化公司,总是不满意,两者难以平衡。商业化带来了无价值感,而缺乏商业的理想同样感到让人虚无,竹子说:“那种没有一个行业和岗位想做,就和咖啡师没有一个店想去的感觉是一样的。”
疫情是让竹子离开北京的直接原因之一:她所兼职的酒吧和咖啡店都不得不关闭。正职的文化空间也从实验性的,变成努力求生的小店。
竹子仍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,但至少她还挺喜欢bartender的工作。于是,她去了三亚,继续做bartender。

此前,她犹豫过,对于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、能够成为白领的人来说,完全变成bartender是否是一种堕落?
但三亚好像没人在乎。这里曾经去过、住过北京的人不少,现在,他们都在这里,等到夜里来喝杯酒、聊会天。
竹子的生活变成了发呆、潜水、无所事事或是学习。她想:“离开北京对于我们这样机会很少的小孩来说,其实只是让自己有得选,哪怕只是看起来的、暂时的。我终于发现,当吧员不是一种跌落。而是回到自己真正的位置,再去看能做什么,代价是什么。”
可以把离开北京看作是竹子的gap。她在北京已经培养了足以养活自己的技能,只是,浩瀚的机会让人疲惫。她需要休息和考虑。
竹子打算继续学业。那之后,会不会再回到北京?也许吧,谁也无法预测几年后的事。

同样去往了旅游城市的还有日尧,她在大理和滇西之间往返,从事动物保护工作。
在离开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前,日尧决定:“我要到山里去,人越少越好。”而后得偿所愿。
滇西的村寨得开车抵达,距离县城一个小时的路程,拢共二十九户人家。每天早上八九点钟,长臂猿像公鸡打鸣那样把人叫醒。村民们把长臂猿叫做“甲米呜呼”,傈僳语,“呜呼”就是模拟它的叫声。
和族人建立联系,日尧也会和他们一起喂牛、打笋子,偶尔用汉语聊聊天。傈僳族人说汉语依然遵照自己的语法,先说主宾,再说谓语。
大理的办公室没那么山野气息。其实日尧过去并不喜欢大理:“总让人想起安妮宝贝,或者文艺青年。就是太文艺了的感觉。”但她觉得大理和想象中很不一样。
在大理,日尧租住在750元一个月的房子里,看得到苍山,走路几分钟便能到达古城。她参加过706空间的聚会,在那里,比她还要“离经叛道”的人更多,数字游民们分享着经验,大家把大理叫做“大理福尼亚”。
“离开北京以后,感觉到世界开阔了,原来还有那么多种生活。”这是日尧的感受。
在北京,日尧最自在的行为,是工作后去看live。非得在现场,才能冲刷格子间里螺丝钉的感觉。每周或每两周一次,从公司出发得一个小时,回家得两个小时,北京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。
超大城市里可供选择的娱乐地点种类不多。日尧的工作地点曾在798边上,有同事趁着午休一口气逛了三个展览。今年,庞宽进行了十四天直播,日尧很容易地认出那就是798里的星空间。
798园区里四处是涂鸦,时不时有人拍照,日尧觉得那很傻——她太频繁地来到798,对于涂鸦已经习以为常。她几乎不拍照,能找到的完整涂鸦照片只有一张,是一行字:“今天是好人,明天不一定!”
换了工作近一年,日尧还没有去过live,也没有再去找live house。好像不再需要了。日尧暂时没有计划再回北京:“现在,我还有好多地方想去。”
30+、40+
最后的离开机会?

暖暖是为了拒绝北京户口而离开了北京。
这听起来像绕口令,读顺了以后,比绕口令还令人费解。暖暖在北京读了13年书,从本科到博士,通往北京户口的路逐渐清晰:就读博士后,进入学校,从事学术工作。
其实这是暖暖第二次面对是否离京的选择。第一次在硕士毕业,但她考取了北京大学的博士:“因为是北大,我还想再留一阵子。”
北京的教育辐射了孩子和成人,专业者和非专业者。在考博前,暖暖会去往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,两边都人满为患,图书馆里的成年人让她疑惑“大家都不用上班吗?”,北大的大教室则是连窗边都有人听课。
等到她自己在北大读博时,仍然有退休的老人来到教室,想要旁听博士课程。有时,老师会建议:难度太高,不适合旁听。
2018年,暖暖作为会务参与了开设在北大的世界哲学大会,会议向社会开放,几乎只要提交论文就能参会发言讨论。暖暖记得,他们收到了几千份论文。这也是世界哲学大会有史以来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。
北京有很多机会,但想要北京户口,机会就比较有限了。摆在暖暖面前,最便捷的道路是:继续研读博士后,而后在高校工作,顺利落户,成为真正的北京人。
但暖暖并不想再做学术,她想要创业。北京同样聚集着创业者,在咖啡厅里,项目常常被提起,中关村也曾是创业的传奇地。只是,这意味着要放弃落户的机会。
落户与否的背后,是两种职业乃至未来生活的选择。是要稳定而体面,还是冒险?生活里到处在暗示答案——
有人在医院看腰椎,医生说是脊柱侧弯,但是,“我就不写在病历里了,以免影响以后你找工作落户。”患者费解,医生坚持,最后,病历上没有出现结果。
就连在网上浏览视频,暖暖都会看到,决意迁走北京户口的人,遇到了不知如何操作的办事员——似乎他们从没办理过这种业务。
她有这种感觉:“我很清楚地知道,如果在当下,我不离开,那么我真的就不会走了。”
尽管暖暖不讨厌北京,但她还是选择了创业那条路。于是,她离开了北京,来到上海,决绝,以防后悔。
这是在上海的第二年,暖暖捡回了在北京入秋的习惯:“从喝了一夏天的酸梅汤,吃了好久的麻酱凉面,转为疯了一样找离我最近的南门涮肉,决定隔上10公里,也要吃到它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怀念。”

在北京六年的echo,离开的时间节点也到了。
来到北京时,echo就不是以留下为目的。她是浙江人,早前在宁波从事旅游行业,想着北京更大,也许有外派的机会,才做出了去北京这样不太“浙江人”的决定。可惜一直未能如愿。
2019年,来到北京的第三年,echo打算申请澳大利亚的打工度假签证,结果撞上了疫情。等到2022年,手续恢复时,她距离截止年龄30岁只差一年。
但这延迟的三年里,echo已经成了胡同观察家。
“老北京都在胡同里,门口养着花花草草,挂个鸟笼或者蝈蝈盒子,大爷坐门口扇扇子,猫狗特多。”她在胡同里还拍过一只散步的鸡,见过一只猪。这可是二环。
胡同可以逛一整天。大杂院先看电表,这意味着人数,要是有二十来个电表,说明可以晃悠很久。胡同里走几步就有公厕,这说明还是老房子,没有下水道。
东城和西城的胡同保留得好,靠近皇城,过去住着达官贵人。南边过去住佃民,粗犷得多。杨梅竹斜街年轻,咖啡店和兔儿爷做邻居。

作为旅游业从业者,疫情之后,echo的工作就变成了city walk,挖掘在地文化,不少是胡同,还有那些看起来俗套的景点,比如陶然亭公园,但是有园林专业老师讲解。
这也是echo眼中,北京的好。“北海公园,可能有人瞧不上,都是游客。它也是北京人的公园,接地气的皇家园林公园。”echo就住这附近,总看到有人溜达,北京疫情时,她就踏着雪绕北海公园跑步。
一片园林,echo也可以去数次,做景点参观,做冒险的探索,做生活的放松。她和朋友连续两天去圆明园,为了找齐四十景。除了修复的部分,剩下的圆明园还是片废墟,杂草丛生的乱石堆。两人打印出古画里的图案,在树丛里挨个找。
echo留给北京三个月的时间。她必须得走,抓住最后的机会,但只有三个月时间才足够告别:“之前觉得是意外,被留在了北京。现在突然要走,怀念又留恋,慢慢地接受,来了总有走的一天。”
八月,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晚上,天气很好,云看得清楚,行李还没收拾好,echo夜游胡同,就是家门口的胡同。
也许这次走了就不会回来了。也许回来,还是会选择北京。
“对于寻常人来说,离开北京最后的窗口已经关闭了。”琳琳说。她今年43岁,不同于“寻常人”的是生育更晚,孩子尚未读小学。
作为外地来京人,琳琳是会被羡慕的那种:拥有北京户口,购置了学区房,在体制内工作。
她曾经在北上深三地生活过,最后选择了北京,因为这里丰富的文艺活动,包容的环境,很符合她的需求。
但随着孩子出生,她开始感到恐慌:北京冬季气候严寒光照不足,竞争激烈,父母们从幼儿园开始鸡娃,更可怕的是到了小学阶段,由于孩子太多,很多学校都不允许普通课间离开教室,遑论操场撒欢。北京并不是她理想中的孩子成长环境。
在琳琳读书时,老师的激励方式是说:“今天不努力,明天读川大。”向外走,尤其是走到北京,是成功的表现。但二十余年过去,琳琳觉得成都并不比北京差,甚至花园城市的建设更让她喜欢。2021年她回成都探亲。
“呆在成都的那几天过得很惬意。说起来,其实也只是在逛公园而已。”琳琳说。她是公园爱好者,但在北京,从十月到次年四月,她都会避开公园,太冷,也太萧瑟。
成为母亲后,琳琳把亲近自然放在了学习成绩之前:“我对教育没有执念。自己经历过,也知道,学习只是众多变量中的一个。我现在最大的期盼是希望孩子不要近视。”
定居时的奋斗目标,到了离开时便成了障碍。琳琳的爱人并不赞同搬离北京,尽管他的工作已经被调动至成都。他的看法是:都做了那么多,为什么要走?
而琳琳在思考好友的建议:“有了金锄头,就一定要种地吗?”
这句话的意思是:拥有了,就要被束缚吗?

选择城市,究竟意味着什么?
Mia搜索记录里有这样一条:没有北京户口,可以埋在北京吗?让人不禁想到2012年流行的那支《北京北京》:“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,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。”
离开北京的五年时间里,北京成了Mia的执念。她梦到自己在北京工作,寻常的一天,坐在工位,打开电脑。她又来过几天,刚下火车,感到自己是一棵枯萎的树,被北京的阳光一照,重新发芽。地铁卡里还有余额,她想:“这才是我应该过的生活啊。”
2015年,在天津读书Mia结束了大学生活,她在北京一家影视公司的实习成功转正。这是一家体量较小的公司,以耽美题材为主,保持着影视公司的加班节奏。
次年,该类题材的首个爆款剧《上瘾》才诞生——而那时,Mia已经回到了老家江苏淮安,在家里,她看到了这部剧。北京生活只持续了不到一年,因为妈妈的身体原因,Mia直接选择了辞职,回家。她甚至没有考虑过请探亲假,在家人和工作之间,她无条件地以家人为首。她想得也很简单,等到妈妈身体好了,再回北京。
妈妈并不这么想。在老家,妈妈常说的,就是让Mia留下来,在家乡发展。回京的日期一天天推迟,先是妈妈的恢复期,再是Mia在当地开始工作。
“最开始觉得很好,在家乡,难得能够沉淀下来。但慢慢地,就感到被消耗,对人情社会的厌倦……”Mia说,“我觉得我就像一把刀,在家乡变钝,而在北京,我被打磨,逐渐锐利。”和妈妈的争吵也随之爆发,她辞去了工作,北京逐渐进入她的梦境。
想要重回北京不容易。Mia已经在家乡待了四年,她尝试过投简历,可是用人单位需要的技能已经更新了。在Mia还在北京时,宣传工作以微博为主,而现在,制作短视频几乎不可或缺。Mia受挫了:“有时跳出来想,又不是应届生,经验又不充足,我是公司的话,也不想要自己。”她想到了一个更为曲线的方法,去北京继续学业,再工作。
2020年春,离开北京的第六年,Mia重新回到北京备考。“真的是迫不及待,连要隔离都不管了。”Mia说。她在小区里居家隔离了14天,最后一天,居委会通知:即日起,外地回京人员不用再居家隔离。
可是这次回北京,Mia没有得到想要的“锐利”:“我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备考。有时出去,坐地铁真挤,到处都是人,物价高,生活压力很大。我突然发现,我怀念的是全心工作的自己,而不是单纯在北京生活。”又一次,不到一年,Mia回老家了,只是这次,她没有怨言。
Mia依然打算第三次去北京。但她不想再把改变生活的期望,寄托在北京这座城市上。她希望自己能够整理好自己的心绪,以准备好的状态,去到北京,投入自己的战场。
在《早间新闻》里,Alex曾经准备离开,一位管理者对她说:“每次有人令你失望,你就选择逃避,是无法令自己保持纯净的。你认为另一个城市的人就会更好吗?不。”
选择城市,总与我们的人生阶段和欲望密切相关。我们期望着,来到新的城市,就能重启生活。我们难以穷尽生活的可能性,也因此,我们无法穷尽离开北京的理由。
但是,我们相信人们选择的理由在过去几年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。








